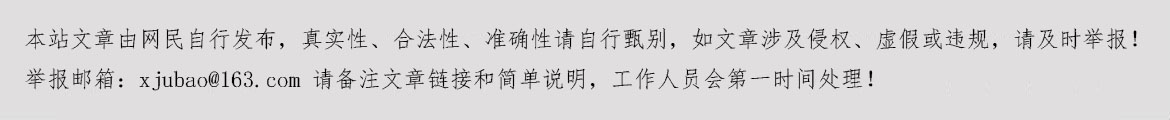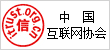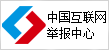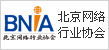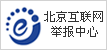创维网是领先的新闻资讯平台,汇集美食文化、教育科研、房产家居、国际资讯、综艺娱乐、体育健康、等多方面权威信息
没有“蛮族”,“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无法存在的
2021-12-11 21:13:01
红警攻略 https://www.hongjing520.com/strategy/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大体上都是“文明”形成之后的文字记载所决定的,而这些记载都对草原“蛮族”极不友好。正如《欧亚之门》所言,“就在三十年前,被视为古典文明‘边缘蛮族地带’的中央欧亚北部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还被认为是原始的”,他们是最古老的“他者”,然而从考古文明来看,且不说最初并没有“蛮族”,到后来也正是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将不同群体统一在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中,极大地促进了欧亚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联系,“他们创造了一种‘蛮族边缘地带’,没有它,‘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无法存在的”。
*文章原刊《三联生活周刊》2021.11.15期,作者授权发布
牧场上的马群
丝路之前的丝路
文 | 维舟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一点 “丝绸之路”的历史,那常常被赞颂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是以和平的交易代替野蛮的交战,呼应着当下所推崇的开放性,甚至有几分像是“最早的全球化”——确实,美国学者米华健就曾说过,“就其性质而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所实现的成就,与今日‘全球化’的成果大同小异”。更妙不可言的是,谁都得承认,丝绸之路的源头就在我们中国。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商人从未主导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那大多是一些远道而来的胡商,将东方的丝绸等贵重物品像接力赛一样一程程地向西传送。这有时倒是与国人历来的自我认知暗中契合,因为这似乎意味着中国无求于外,作为输出方享受着应得的文化优越感。不过,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丝路出现之前的“丝路”,又是什么景象?
实际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诸如小麦、马、马车、冶金技术等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事物,最初很有可能都是从西方传入的,而这远比丝绸之路成型的汉武帝时期早了一两千年之久。当然,这样的文化交流不可能是单向的,正如《欧亚之门》一书中通过考古发现所证明的,“实际上中国产品早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欧亚地区了。如果没有欧亚地区早已存在的贸易和交通的路网,像丝绸之路这样长距离的贸易之路是不可能这么快建立起来的。”(页397)
所谓“欧亚之门”,就是指作为欧洲和亚洲天然分界的乌拉尔地区,在人类早期历史上所曾扮演的角色:这里地处与中国、印度、伊朗、两河、欧洲等诸旧大陆文明往来互动的十字路口,如果没有在这里形成并长期持续的交流,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将会大不一样。
对这一地带的关注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1904年就在其名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划定了影响欧亚大陆格局的“心脏地带”,认定它作为“通道地带”连接欧洲与东方,一再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他的这番断言以往一直是被人从现代地缘政治的角度予以理解的,但现在考古发现逐渐证实,即使放在数千年前的青铜时代,这很可能也是成立的。
为什么这里能成为影响历史的枢纽地带?这并不仅仅是因其地理位置,也是因为乌拉尔地区富集的铜矿在青铜时代吸引了来自许多地方的“工业移民”。两位俄罗斯考古学家在对公元前4千纪到前1千纪的的诸多遗址挖掘、分类、辨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在这里,青铜和铁器等冶金技术率先取得突破,推动了复杂社会的兴起,后来被视为原始印度-伊朗人文化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由此发展壮大,并最终将这一新技术通过欧亚草原传播到了地处欧亚大陆边缘的各大文明。
这是在夸大其辞吗?毕竟,土耳其也曾宣称是其祖先传播的文明形塑了诸文明,以至于有人嘲讽说,这就好像是远古有个突厥人对着天空吐出一句“要有光”,于是历史就开始了。不过,对“欧亚通道地带”的理解并不只是一个建构起来的神话,而是基于考古现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历史,因为不可否认的是:在远古缺乏海路交流的情况下,从长城到东欧的这个草原地带,才是人类文明碰撞、集聚、联网、孕育、创新的集线器,而在这其中,金属是导致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
现代人很容易低估了当时冶金技术的变革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对我们来说这仿佛只是一些普通的金属,但正如历史学家杰克·古迪曾指出的,在当时,“青铜时代预示着所谓城邦革命的来临”。金属冶炼是那个年代的高科技,所需要的知识远比农业、陶器更深奥,这催生了第一批技术专家;随着金属用途的扩大,这带来了犁铧等器具的引入,在运输、耕作和战争中畜力的使用,有史以来首次提供了一种非人力能源;与此同时,金属矿藏的分布并不均衡,这又强有力地带动了远程贸易的发展。事实上,青铜开辟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网络。
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冶金技术和畜牧业催生了最早的食物生产型经济,财富积累才有可能,经济分化、社会分层由此逐渐得以出现,对青铜的控制又促进了王权统治的权力集中,反过来,又只有权威才能大规模征发劳动力从事采矿,这样的相互作用最终催生了城邦乃至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而“复杂社会的崛起”正是当前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中心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早期历史上,无论是草原与耕地、牧民与农民,还是“野蛮”与“文明”之间,都并没有后来那样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人群、文化都尚未明确分化,而大草原则为人口、技术、思想的流动提供了天然的通道。在新观念的传播过程中,草原地带的居民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也正是这些新理念成为各地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分裂”与“聚合”乃是常有的事,交流与融合不断发展,不同考古文化之间的差别也因此相当模糊。
当然,虽然我们当代人会将这这一历史过程视为“文化传播”或“贸易”,但不必讳言,它也常常伴随着剑与火。拥有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装备了双轮车的印欧人,在当时拥有对周边民族的压倒性军事优势,现存年代最早的双轮车,正出土于乌拉尔-伏尔加流域草原南部的辛塔什塔遗址。这种结构复杂、加工精密的复杂器械,犹如那个年代的坦克,通过军事征服串联起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复合文化体系。
在本书中将这种诸多文化共享的交流网界定为“技术文化网”(techno cultural networks),也就是说,考古学虽然只能根据史前社会的物质遗存来推断,但最终要理解的则是当时的社会运行方式。正由于当时数量可观的人类活动并没有明确的分化,又尚未形成后来那样稳定的形态,而是由相互交流决定的,两位作者将之称为“文化间共同体”(cultural intercommunity)——这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意味着对那些早期文化的理解从孤立的一个个遗址,转而去关注其相互间的影响、互动和“关系”。
为什么有必要了解这些?这不仅是因为近些年来“中国青铜文明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有一部分即来自欧亚草原地带”的共识逐渐形成,让我们意识到中国文明并不是在孤立和隔绝中发展起来,也是因为这些本身就能促使我们反思原有的历史认知模式。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大体上都是“文明”形成之后的文字记载所决定的,而这些记载都对草原“蛮族”极不友好。正如本书所言,“就在三十年前,被视为古典文明‘边缘蛮族地带’的中央欧亚北部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还被认为是原始的”,他们是最古老的“他者”,然而从考古文明来看,且不说最初并没有“蛮族”,到后来也正是他们在很短时间内将不同群体统一在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中,极大地促进了欧亚各地的文化交流和联系,“他们创造了一种‘蛮族边缘地带’,没有它,‘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无法存在的”(页239)。
从这一意义来看,后世的历史,不论是突厥凭借冶炼术崛起、还是蒙古帝国带来的“早期全球化”,都是对更早之前就已存在的那个欧亚文化交流网的一种呼应。“蛮族”的冲击导致本地文化发生重大改变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网络,在这方面,历来自视为“中心”的中国其实处于这个巨大网络的边缘,也从未真正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这对中国人而言,可说是在西方东来之前的“挑战-回应模式”。理解这一点,其实也就更好地理解了我们自己。
▼
欧亚之门:乌拉尔与西西伯利亚的青铜和铁器时代
[俄]柳德米拉·克里亚科娃 安德烈·叶皮马霍夫 著 陈向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4
ISBN:9787108069160 定价:89.00元